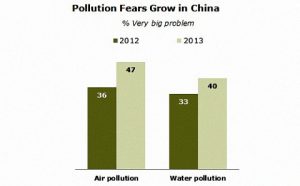本文是皇家艺术学会亨利·基平对《假如市长治理世界》一书作者本杰明·巴伯的采访。
亨利·基平:你是怎样开始关注城市及其在解决全球问题中可以发挥的作用的?
本杰明·巴伯:我一直在研究如何使民主在各种不同的机构和各种不同的规模上发挥作用。我们都知道民主诞生于城邦,经过古代和中世纪的发展一直延续到新英格兰的殖民地。但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城市已经不再是主要的机构了。一个国家有成百上千万人要参与讨论,这迫使我们把民主从直接参与的模式升级成为代议制。
正如城邦规模太小难以满足新型国家机构的需求一样,我们如今面对的挑战都是相互联系的——无论是疾病、全球变暖还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启蒙时代诞生的民族国家机制已经成为了阻碍我们解决这些跨境挑战的绊脚石。2005年前后我参与的一个项目试图探寻什么样的全球治理架构才适合解决本世纪如此大规模的、相互联系的挑战,以及这种治理架构是否可以民主。
我的书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其中有一章是专门论述城市的。但我越是深入研究城市的运作,越是清晰地发现在利用非正式网络和解决跨境问题方面,城市遥遥领先于我所研究的其他所有机构。城市中有大量的合作和非正式治理。而且,由于城市的本地性质和规模特征,它们比那些在国际网络中与它们竞争的企业机构更为民主。
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开始人类利用城邦解决问题,后来城邦开始渐渐显得规模太小。在后封建制的欧洲和新世界,民族国家取代了城邦制,却又被发现不足以解决全球性问题。这样一来,如果我们能在某种程度上返回民主的诞生地——城市——是不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呢?在探寻解决全球治理问题方案的过程中,城市这个考察对象一下子便显得与众不同。
还有一件事也变得明显。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假如市长治理世界》,但副标题是“为什么应该由他们来治理世界以及——更重要的——为什么他们已经在这样做了”。我提倡的解决方案已被付诸实施,虽然不是以全球治理的名义,而是像C40以及和平市长会议这样以沟通交流或是跨城市合作的名义开展的。也就是说我这本书不但论述了为什么城市可以做到国家做不到的事情,也指出城市已经在做国家不能为之事。人类迈向全球城市治理的旅程比我想象得要短。
还有一点可以作为佐证。911之后我建立了一家名为“共生运动”的非政府组织。每年我们都会到世界上的一个城市开会,探讨人类相互依存的现实以及民间、宗教和学术领袖可以为我们提供怎样的帮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支持来自于市长,而不是首相或者国家元首。我意识到我们做的很多事都是基于城市的。共生运动是证明城市日益重要的一项关键证据。
基平:从智慧城市运动这样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你的想法确实有道理。比如阿姆斯特丹就制定了到2025年将碳排放减少40%的宏伟目标,比欧盟的整体目标高出一倍。城市层面似乎是可以达成社会、私人和公共部门之间的联合的。
巴伯:确实。各国在哥本哈根和里约热内卢开会试图制定接替《京都议定书》的全球协约,但不幸的是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前来开会都只是为了说明他们国家的主权不允许他们采取任何措施。不过好在除了国家元首之外,市长们也在开会。市长们持续探讨,签订了公约,并且切实地展开了行动。
更进一步地说,全球80%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都来自人口五万以上的大城市。因此,如果城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除了阿姆斯特丹之外,洛杉矶也清理了港口,减少了三到四成碳排放量——就可以产生显著的影响。即便美国和中国什么都不做,各个城市就可以为问题的解决作出巨大的贡献。这不单单是理论上的可能性。
基平:从城市层面进行思考和工作确实有很大的好处,这就让我想到了领导力的问题。之前您曾经说过“城市可以做到国家做不到的事情”,这是由于城市领导人具有怎样的特质呢?
巴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想先讲一个您没有问到的重要问题。我认为,定义民族国家司法和立法权力的主权已经成为了阻碍国际合作的巨大障碍。城市没有主权,但它们也因此可以摆脱那种造成民族国家之间无法有效合作的意识形态和司法权力束缚。城市天然地就是相互依存的。
现在回到您刚才的问题。城市领导人所需的能力和面临的现实都与国家领导人大大不同。务实精神是最重要的。市民们不在乎你是共产党人还是托利党人;该捡垃圾还是得照样捡。只要城市运转顺畅,市民根本不关心意识形态的问题。长期担任耶路撒冷市长的泰迪·科莱克说的好:“少听布道,多通下水道。”说白了,市长其实也是城市的一员,跟你的邻居一样。城市的规模改变了城市的治理方式。
在某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和中国——市长的位置只是职业生涯的一个阶段,这是由政党系统决定的。弗朗索瓦·奥朗德曾任蒂勒市长,但他并不是当地人。在大多数国家,市长一般是不会升迁高位的。这既是因为他们不想,也是因为他们不擅长意识形态和国家政党政治。不过也确实有些例外。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就曾经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也就是说他可以做出土耳其政坛上所必需的妥协。
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曾经担任大城市的市长。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只有两位总统曾经担任过市长的职务。格洛弗·克里夫兰曾短暂担任过布法罗市长,而卡尔文·科利芝当过马萨诸塞州南安普敦市的市长,但市长的经历都没有包含在二人的简历中。
这就归结到了城市领导人的特性。市长并非那种利用意识形态宣言或者壮烈的言辞就可以动员成百上千万人的有魅力的领导人。他们以高效解决问题见长;他们都明白合作的重要性,认为光靠个人寸步难行。公私合作在国家层面总要涉及到宏大的意识形态问题,但对于市长来说则是第二天性。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十分成功的市长不会继续寻求高位。布隆伯格一开始是民主党人,后来转向共和党,如今则是独立人士。
基平:英国近日就直选市长问题在十个城市举行了公投,只有布里斯托投票通过了新的市长选拔体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奇怪的局面:市长上任之后总会受欢迎,但选民却因为缺乏信任而不愿建立相应的政治制度。这样的现象在其他国家有没有发生过?
巴伯:虽然我们需要也想要对城市和市长形成放之四海皆准的认识,但我们也不能忘了每个城市情况都不同,而且城市与政治体系中的其他部分也不同。尤里·卢日科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20世纪70年代在莫斯科市政厅任职,在副市长和市长的位置上一共干了28年。最后,他被梅德韦杰夫赶下台,因为后者将他视为威胁和潜在竞争对手。在20世纪初的美国,人们认为市长们严重腐败、道德败坏。进步运动提出了城市经理的概念,也就是任命技术精英管理城市,解决城市的问题。这个主张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清除了城市政府的腐败习气。不过后来,人们感到技术精英管理城市不够民主,于是又恢复了市长制。
我不会写一本名为《假如城市经理治理世界》的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市长跟市民关系亲密。一方面市长可以进行跨境合作。但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他们可以以相对民主的方式进行跨境合作。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书里有很长的一章介绍参与性预算制定。这是让市民直接参与城市资源分配的绝佳例子。
基平:让我们再回到全球视角上。您提到解决问题的全球网络,也谈到了这一机制的民主基础。这样一个网络大致是一个什么样子?对于那些并非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来说,解决问题的过程又怎样能做到民主?
巴伯:对于您的第一个问题,我认为下一步——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一步迈得太大了,但我认为目前城市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应该是召开全球市长议会,并成立秘书处。议会不制定约束性法律,只负责分享最佳实践和实验结果供城市自愿遵守。秘书处可以定期组织评选城市生态奖等实践活动。比如秘书处可以号召部分城市自愿减少四成碳排放,然后由各城市协作完成这一目标。
我与多位市长进行过探讨,他们都表示很喜欢这个主意,并且他们现在就经常私下见面。我不会告诉您这些市长的名字,但确实有好几位重量级的市长支持我的观点,他们在我的书出版之前还碰头研究合作事宜。
您的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还要重要。超过一半世界人口在城市居住,但那也就意味着还有不到一半的人口并不在城市居住。我的书最后一章花了很长的篇幅讨论全球市长议会是不是会有不具代表性、不民主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第一我们要看到城市已经通过农业、交通系统等与周边地区建立了很深的联系。事实上,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将市长也视为城市周边地区的代表。这样一来全球市长议会的代表性就会显著增强。第二,全球市长议会不会是一个发布强制命令的组织;所有事情都是自发自愿的。所以地区政府或者乡镇也可以采纳市长议会的意见。
第三,乡村地区也可以有它们自己的平行架构。我并不是倡议建立一个统治地球的组织。我提议成立的是一个合作组织,城市可以在这里携手共治,一起解决全球问题。在有些问题上,地区可以决定同意或者不同意协商结果。
第四,如果我们讨论的是每个选民都可以发表意见的那种民主机制,那么全球市长议会永远不可能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但如果按照博克的理论,也就是由代表来追求集体的利益,那么市长们不但会照顾自己城市的利益,还会努力争取公共利益。这样一来他们就代表世界,代表着他们各自城市之外的农村和其他地区。我在书中探讨了这个重要的问题,不过可能还有不充分之处。
最后,我们难道应该因为部分人口没有被代表就拒绝成立全球市长议会吗?还是应该先建立起这个组织再为农村地区寻找更好的机制?
基平: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已经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眼下的全球治理无法照顾到所有人的利益。
巴伯:没错,跨国公司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已经在追求慈善利益。但目前没有任何代表机构。如果我们可以从零开始建立起代表世界一半人口的机制,显然是会大有帮助的。
原载于RSA Journal
翻译: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