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们很早之前就提出: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并非文化思考或者抽象理念,而是物质条件。但这一次,我们发现了一个新情况:旧的物质性概念中所包含的技术和生产力、阶级利益、债务人与债权人等等,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内容。实际上,它们可能仅仅是更深层次物质条件的肤浅表现。而那些强大的力量,诸如气候变化、土壤肥力、微生物以及古今所有社会都生存于的这个不断复杂的生物圈,才是历史最根本的发展引擎。我们无法将人类的兴衰与自然环境或者物质和能量的规律割裂开来。
或许正如戴维·波特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其著作《富有民族:经济富裕与美国的特性》(1954年出版)中所说,美国历史背后最深入人心的一个理念就是对于(美国资源)富足,以及这种富足似乎可以带来无限增长的认知。几百年来,这一直是美国式思维的核心,如今又走向全球,让几乎所有国家的人有了与过去美国人一样的想法。经济学家们也许会争论“增长”在未来是否会无限持续,但通常他们都会同意波特关于这个理念已经成为美国人灵魂的说法。不过,像波特这样的经济学家在面对问题的时候通常就会陷入沉默。比如:富足或增长的理念来自何处?它是如何、在哪里以及为什么能让这么多人如此信服?如果这个理念有物质基础的话,这些物质基础是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开始消亡?
近来,经济学家们就1970年左右以来美国的增长率下降进行了大量讨论。比如,罗伯特·戈登在他广受推崇的新书《美国成长的兴衰:内战以来的美国生活水平》(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中警告说,美国长达一百年的增长浪潮正在走向终结,无论决策者还是社会科学家都无法阻止这一进程。在书中,他对美国“进步”的这一百年中在能源消费、服装、住房、通信和交通等各方面“取得的进展”进行了空前全面的汇编罗列。但对于这一百年间的“增长”如何发生,如今为什么失去动力,他却避而不谈。但他多少提到了是“技术”的神秘力量促生了美国的增长奇迹,如今技术步履蹒跚,带来的回报越来越小,将我们带回了一个老旧的变化模式,其增长速度、重要性和显著程度都大打折扣。
毫无疑问,戈登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但我认为他还不够唯物。在他狭隘的美国创新史叙事中,缺失对生态条件的描述,而在让我们成为一个“富有民族”的过程中,这一因素的重要性至少不会亚于那些名不副实的铁路和钢厂投资者。在对如今美国增速放缓的分析中,生态条件变化要比美国创造力的丧失更具解释力。
整个19世纪美国人为什么带着如此巨大的激情和渴望修建铁路?为什么会如此快速地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木材市场?摆在桌面上的答案就是曾经遍布北美腹地的丰富自然资源。但铁轨和木材加起来也无法创造出这些资源,它们只是让资源变得可资利用,将其变成商品来支撑不断爆增的人口。其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中西部绝佳的土壤和沉睡在荒山和沙漠之下的矿产。当时北美大陆富饶无比的自然资源吸引人们涌入内地、推动新技术的形成、为新城市的建设提供原材料、开垦了大草原、荡平了森林、在河上筑起了水坝。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富足是“人工的”,但只是在一种近似的意义上。最终,人们追求的资源与远古时代采集耕种的祖先所追寻的并无二致。如果说最根本的变化,那就是人口—资源关系等式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获取方式的创新。
无限经济增长的现代观点萌发于公元1492年之后到达新世界的欧洲开拓者和移民中间,要比戈登所认识的早得多。这一观点与驱动他们的原住民祖先寻找资源的“富足”理念并没有多大区别。这些原住民用了数千年的时间才逐渐分布到南北美两块大陆,定居在海边,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从部落到帝国等许多不同的社会形态, 以此来掌控和开发他们发现的天赐财富。对于被疾病、土壤贫化、森林破坏、小冰河期、经济停滞和贫困横行弄得一团糟的欧洲商人和农民们来说,新世界的富足影响巨大。很久之后,这个影响则要更复杂得多:它给欧洲的政治、全球实力、经济、科学和技术等领域都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也就是我们所定义的现代。
随着技术开发越来越倾向于为资源开发服务,新世界的自然资源富足导致世界人口和消费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超常增长。1870年美国的人口接近4000万,世界人口为13亿。到了197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成2.03亿和37亿。当时关于地球人口过多、资源减少的理念开始出现,地球资源不断萎缩的现实在《只有一个地球 》和《增长的极限》(两本书均于1972年出版)等书名中都有明确体现。如果无法找到在资源和宜居度与之前相当的另一个“新世界”,美国和地球的历史就必须跨过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水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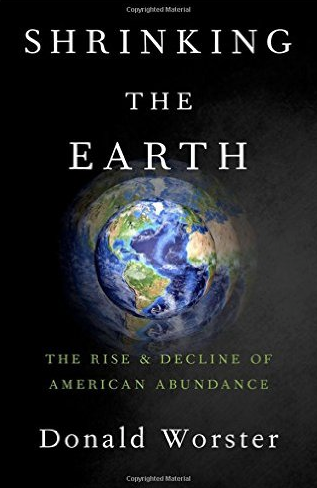 在我的新书《萎缩的地球:美国资源的兴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中,我认为美国正处于一个自我重建的初级阶段,目的是为了努力应对不断变化的人口和环境条件。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的制度、社会关系、价值观和信仰都处于重重危机之中。这反映了一个以不同节奏持续了五个世纪的增长时代的终结。回顾过去,我们必须承认地球物质性的力量,但这并非仅仅指变冷或变暖的气候、不停变化的海流、暴发的生物群或者漂移的板块构造。生物圈比上述任何要素都要复杂,甚至比它们的所有互动加起来还要复杂。无论国家的兴衰,抑或简单的变化,都取决于我们在这个物质宇宙中如何生活。
在我的新书《萎缩的地球:美国资源的兴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中,我认为美国正处于一个自我重建的初级阶段,目的是为了努力应对不断变化的人口和环境条件。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的制度、社会关系、价值观和信仰都处于重重危机之中。这反映了一个以不同节奏持续了五个世纪的增长时代的终结。回顾过去,我们必须承认地球物质性的力量,但这并非仅仅指变冷或变暖的气候、不停变化的海流、暴发的生物群或者漂移的板块构造。生物圈比上述任何要素都要复杂,甚至比它们的所有互动加起来还要复杂。无论国家的兴衰,抑或简单的变化,都取决于我们在这个物质宇宙中如何生活。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