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位于曼哈顿上西区,那里收藏着一件拥有两百年历史的马甲。该藏品完工于19世纪初期,由阿拉斯加锡特卡原住民特林基特人的工匠用中国古钱币制作而成。这件马甲是早期全球时代的遗物:钱币用云南产的铜铸造,被卖给了波士顿来的运货商,又在阿拉斯加海岸用来交换海獭的皮毛。特林基特人的酋长把中国钱币穿在身上;中国消费者身披海獭的皮毛。事实上,这一阶段中国对皮草的需求量巨大,以至于截止1840年,海獭、紫貂等物种不仅在锡特卡附近被猎杀至几乎灭绝,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从蒙古到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半岛,无一幸免。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早期的这场猎杀活动?那时候的人们怎么理解环境危机?从海獭的角度出发,中国的过去又会有怎样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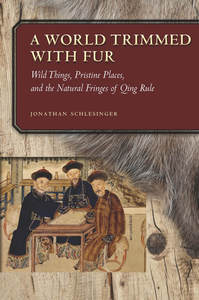 我们可以在北京、台北和乌兰巴托的档案馆找到意想不到的答案。现如今,这三个地方的历史学家们正在细细研究着档案馆里的文档,不仅是中文的,还有蒙古语和满语的记录。我为了写《皮草装点的世界》这本书,进行了3年的研究,发现这些记录深刻地挑战着我们传统上对中国的过去以及全球环境史的整体理解。
我们可以在北京、台北和乌兰巴托的档案馆找到意想不到的答案。现如今,这三个地方的历史学家们正在细细研究着档案馆里的文档,不仅是中文的,还有蒙古语和满语的记录。我为了写《皮草装点的世界》这本书,进行了3年的研究,发现这些记录深刻地挑战着我们传统上对中国的过去以及全球环境史的整体理解。
历史学家早就意识到,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中国资源需求的快速增长改变了这个国家。那个时代的增长是前所未有的。1700年之前,中国人口翻倍花了大约1500年的时间,而1700-1850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两倍。与此同时,随着自耕农向中国边疆地区迁徙,东北、蒙古、西藏、西南和台湾等地的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倍。
除了这些新定居点之外,清王朝统治之下,一场前所未有的自然资源争夺战随即也在森林、草场和高地打响。到1800年,在北京的街头可以买到边疆来的产品,且数量种类多得惊人。典当行记录、日志条目、游记以及其他记录都可以证明这些物质的丰富性:夏威夷产的檀香木、婆罗洲产的燕窝、菲律宾产的珍珠母、云南及东南亚高地产的金属铜、新疆和缅甸来的玉、苏拉威西岛的海龟、斐济的海参、蒙古的蘑菇、吉林的人参和珍珠、西伯利亚的黑貂皮、还有北海道、阿拉斯加、太平洋西北部以及加州沿海产的海獭皮毛。1700年代后期,这些资源的需求量不断上升,市场蓬勃发展。但到了1830年代,一切就都会崩溃:动物数量骤减;森林被洗劫一空;海滩也已经被掘地三尺,再没有珍贵的野生物了。
农业扩张的故事一直是我们理解中国前工业时代发展的核心所在;黑貂、海獭、以及中国经济边缘区的故事则不是关注的焦点。
大多数教科书的内容继续把自然相关的东西归为中国历史长河中无足轻重的一小部分。传统历史学认为,自然是一种外力;瘟疫、洪水和旱灾爆发之时,或者是在文明开始之前的史前阶段,自然才是重要的。
中国的帝国疆界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例如,史学家将蒙古族等草原游牧民族刻画成一支不受文明控制的未驯化的力量,对蒙古人和满族人的描述也都是他们在等待适当的统治和发展。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才开始对这种陈旧刻板的描述提出质疑。例如,环境历史学家已经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在历史发展中持续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还学会了从各种角度看待边疆:我们不再局限于中文材料,也会读一些蒙古文、满文和藏文的材料。这些新材料揭示了中国历史复杂的新维度,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和更广阔的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
清王朝满文和蒙古文的档案展示了一幅极为生动又与众不同的清朝环境史图景。19世纪初,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入北京城:东北的珍珠蚌已经没有踪迹;蒙古的蘑菇采摘者正在破坏那里的草原;针叶林里最后的毛皮动物正在遭到猎人的捕杀。
打下绿色根基
清政府强烈的反应让人惊讶:朝廷下令保护满蒙两族人民家园的自然环境,以维护帝国统治。
在蒙古,清王朝因此推行了所谓的“净化”运动来遣返采摘蘑菇的汉人,调查与其合作的蒙古人,并让土地恢复“纯净”的原始状态。
在吉林和黑龙江,清政府尝试打击珍珠偷猎,对移民和贸易进行控制,让贻贝床能够恢复;与此同时,清政府还捣毁了人参农场,以保持这种植物的自然形态。这些行动带来的结果喜忧参半。圣山博格达汗(位于今天的乌兰巴托城外)等一些地方的保护工作取得了成功。如今,博格达汗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的生物圈自然保护区,受蒙古国政府保护。但在其他地方,保护工作失败,资源被洗劫一空。

清政府在1783年设博格达汗为保护区,使其成为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合法保护区。图片来源:Wikipedia
清政府以这种方式控制了一场跨越帝国边境的困境。类似的资源争夺正在改变西伯利亚、东南亚以及大太平洋地区。在这个更加广泛的区域内,各国应对环境压力的方法各有不同,但驱动这些国家政策的政治和理念却常常不谋而合。
中国的经济边缘区不断发展,那里首先建立的自然保护区位于清朝的蒙古和满洲,地址选在博格达汗和长白山这样的地方,建立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在清王朝拥有相对较深的根基。事实上,和这一时期欧美浪漫主义者开始重新想象原始自然的意义一样,清王朝的臣民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然保护都成了挽救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清政府明白,当时的环境危机已经真正威胁到了满蒙两族臣民在帝国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家园公认的纯净。19世纪初,清政府官员认识到保护自然就是保护国家,说明他们正在形成一种环境意识,这和一代人之后在19世纪中叶美、德等国人民的觉醒极其类似。
至此,是时候将清王朝计入对原始自然的憧憬和保护史之中了。和文章开头提到的钱币马甲一样,今天的纯净是那个黄金时代的创造和遗产。
阅读更多中外对话环境历史系列专题文章
翻译:金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