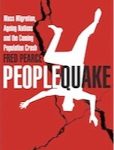作为常驻北京的《卫报》亚洲环境问题的通讯记者,乔纳森·沃茨几年来对中国环境事务进行了大量报道。他的新书——《中国的世界性决断》是一本旅行见 闻录式的著作,讲述了关于中国的飞速发展及其后果的各种故事,从新疆的冰川融化到河南的癌症村,再到四川的大坝工程和上海的摩天大楼。
山姆·吉尔(以下简称吉):在过去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特别是哥本哈根会议以来,中国环境状况的紧急已经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但你四年前就开始写这本书,你是怎样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
乔纳森·沃茨(以下简称沃):这本书是边写边改的,因为中国太大了,而且变化得如此迅速。我发现这种漫游式的报道是一种捕捉变化的好方式,也发现自己写的环境报道越来越多,无论是对工厂建设规划的抗议、河流的排放污染、奥运会前的北京空气质量还是又一个物种的灭绝,所有的选题几乎都是信手拈来的。
要知道,中国的环境状况是一个事关全球全人类的问题,如果非要让我选择一个感到震撼无比的话题,那就要算(现在已经灭绝的)白暨豚的故事了。当我开始报道时,完全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史诗性的题材。只有当我坐下来开始做研究,并努力把它放到语境里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一种已经存在了2000万年的物种的消失是何等的意义重大,它存在的历史比人类长了两倍还要多。这真的让我感到震撼了。
情况还在不断变化。四年前当我开始写书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谈论污染,或许还有气候变化、政治体制以及它们对治理的影响。但我发现自己就好像在进行移动靶射击:就在我更深入关注题材的时候,我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题材本身也在变化。这本书讲的是污染、气候变化和一党执政,但更多的是关于消费和生物多样性以及人类发展的长期趋势。这就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话题了。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非常不幸,因为它偏偏在人类历史的的这个时代进入这个发展阶段。
吉:这本书指出了一些中国对环境现状反应中一些更深层的动力。其中一个就是道家传统和儒家的矛盾,道家期望和谐,而儒家则倾向于对自然世界的统治。你认为这在中国对当今发展阶段的反应中有什么影响呢?
沃:在寻找解决未来困境的方法、避免不可持续生活的过程中,价值观的重要性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国目前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科技上,在硬件上,在那些会发生“反噬”的事物上。价值观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真正重视,但它绝对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从哪里才能找到这些价值观呢?显然西方的价值观并没有挡住西方破坏环境,因此,到中国的哲学和文化本源上去寻找解答是非常重要的。
这本书里的次主题之一是对中国精神中道家一面的探索。中国的哲学总是处于争鸣之中,我发现你不可能真正拥有一个道家文明,它几乎是对天真、无政府和混乱的全盘接受和推崇。儒家大多数时候都占统治地位,尽管中国有时法家色彩更加浓厚。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你能看到一些在居官时崇信儒家的官吏,一旦退隐林泉,诗酒自娱,道家的一面就占了上风。或许这正是中国文明以及它为什么如此渊源流长的秘密之一:儒与道的平衡。
我曾经和中国最火的哲学学者于丹进行过讨论,她对《论语》的解读非常符合现今的共产党理论。她告诉我自己更多是一个道家,但她不认为“中国已经准备好进入道家时代”。诚然,过去60年中,道家的一面已经没落,“统治自然”的一面一直占据上风。
吉:你在书中举的生态例子之一,就是将古代的都江堰灌溉系统和大型的水电工程项目紫坪铺大坝进行对比,二者都在四川。
沃:我第一次到都江堰是2008年四川地震的时候,但直到我采访了哲学家唐锡阳之后才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唐锡阳是主张“中国要解决问题,必须更重视道家”的人之一。他告诉我如果我想去看看道家在实践中的作用,就应该到都江堰。这是一个事物存在形态的典范,它们可以常在,可以耐久,你可以和自然共处,而非与其对立。
这是一种长远的观点。另外一种发展的形式则是脆弱的。水电工程的解决方式十分惊心动魄,当我看到三峡大坝时,我被人类的力量所震惊,但他们也带来了新的不安。对于这一点,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沉痛的教训,这就是书里后面提到的1958年“大跃进”,人类的狂妄傲慢,认为自己能征服自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
毛泽东式的自然观并没有完全消失。尽管不断提出质疑,但中国的巨型工程仍然气势十足。尽管我看到的一些工程是在过去七年中才完成的,但完全是对毛泽东梦想的实现。青藏铁路、南水北调工程、紫坪铺大坝,全都是毛泽东的创意。这一切就好像毛泽东这个大梦想家的梦想,由现在的政府来实现。
但我认为现在人定胜天的旧观点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强烈。在三峡大坝的展示中心,看不到现任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人的照片。他们也没有参加大坝的封顶仪式,这说明他们对工程的正确性是有所保留的,还要静观其变。
吉:你是否认为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已经在生根发芽?
沃:我看到了对新价值观的追寻,一个对新价值观真正的呼唤,也发现人们已经感到任何新价值体系的塑造都不能脱离环境问题的解决。但我还没有看到对新特质的清晰定义,甚至对旧特质的彻底改造,而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我们确实看到了令人乐观的迹象:绿色NGO的增长,媒体上环境问题曝光率的提高,但这些都无法代表意识形态的主流。
然而,中国近100年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一些理念流行之迅速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无论是人们对政治革命的热情,还是赚钱的热情,这个国家都能在几乎一夜之间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希望在环境方面也能如此。
吉:那么,中国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绿色超级大国吗?
沃:我在书里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未来三四十年人类将要度过一段艰难时期,无论用什么生态标准衡量,我们都已经超过限度。未来四十年人口数量注定要再增加20亿,我们必须捱过这个艰难时期,然后人口就会开始下降,而且也会有更好的技术和经济模式。但如今,同时处于最佳和最差境地的国家就是中国。
中国处于最佳的境地是因为经济增长如此之快,它的确拥有许多资源。处于最差境地是因为在它的发展达到这个强劲阶段时,却碰上了全球发展历史上一个非常不幸的时期。中国没办法向其它国家一样寻求外来资源,只能实现独立创造。
中美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中国势不可挡,只能不断向前跑,相比之下美国则满身惰性,只是努力保护已有的东西。这也正是中国在成为绿色超级大国方面比美国更有优势的地方。
吉:你写这本书的意图之一,是为了在西方对中国拯救世界经济能力的一片乐观声音中,提出一点怀疑。
沃:现在仍然有一种广为传播的看法,即“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在过去二百年中屡试不爽。尽管它对十九世纪的英国、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二十世纪后半的日韩都管用,但由于规模和时机的问题,对中国可就不一定了。
从某种意义来说,英国和中国或许成了这一阶段的开端和结束,而这一阶段从长期的人类发展来看是不正常的。英国是一个小国,却产生了惊人数量的污染,不可持续地开采和使用资源。尽管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它还没有构成真正的全球性破坏,但这个趋势扩散到整个欧洲、到美国、到很多国家,这些不可持续且过度生产的国家越来越多,与此同时那些能让它们获取资源,消化它们破坏的国家越来越少。到了今天,中国到哪里去倾倒垃圾?如何从世界其它地方获取足够其人民发展的资源?我认为这正是经济发展和生态激烈碰撞的地方。
环境和经济曾经齐头并进,但如今却背道而驰。经济学家、政府和企业全都认为世界问题的解决在于增加中国的消费,然而环境主义者齐齐警告:要小心你们期望的东西。如果说真的有一种解决方法的话,那就是经济和环境的再次结合。最近关于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讨论,说明中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一机制就是要求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向云南、黑龙江和广西等环境良好的地区付费,补偿其“环境服务”。这意味着吸收碳的森林和吸收污染的湿地都被直接赋予了价值。
这也将意味着笔记本电脑可能更加昂贵,但从反映生态限度和事物真正价值角度来看,这个价格的真实度更高,而这也将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价值观的重要性。
山姆·吉尔,中外对话副主编。
乔纳森·沃茨,《卫报》亚洲环境问题通讯记者。他的著作《中国的世界性决断》由Faber and Faber公司出版
首页图片由Shreyans Bhansali摄